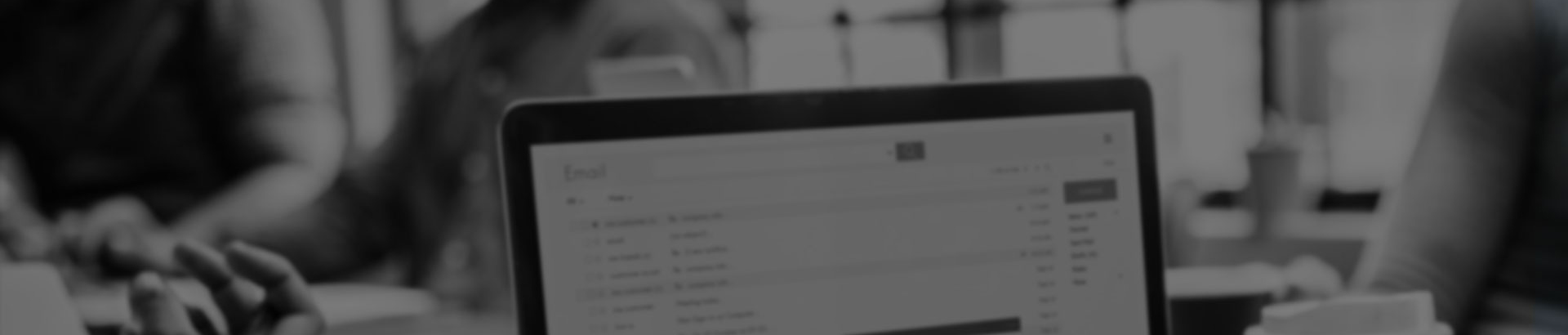石磬残片、金叶、有领玉瑗、丝绸实物残留、青铜跪坐人像、青铜眼形器、青铜人头像……这些最新出土的三星堆文物,让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考古在一、二号坑发现35年后,再次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不知道有没有人特别注意到――这次考古发掘的现场使用了“方舱”,而且那些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方舱+防护服,不是防疫需要,而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这也是在考古发掘中首次使用。穿防护服是为了避免人身上的现代元素被携带到发掘现场,更进一步说,是为了避免现代DNA污染古DNA。
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向远古时期要答案”。没错,如今古DNA分析越来越多被应用到考古发掘之后。不过,古DNA研究又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
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天,人类,在这一天快结束的最后36秒才出现。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此后四五十年,秦始皇陵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河姆渡遗址又一次次刷新了考古重大成果。
1980年,随着湖南医学院学者尝试从马王堆汉代古人类遗存获取核酸分子开始,古DNA研究在中国正式走进考古学。

古DNA是指古代生物遗体或遗迹中残存的DNA片段,包括古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DNA。古DNA是分子考古学的核心,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DNA分子,以解决考古学问题。
与传统的考古学研究相比,古DNA研究是从分子层面直接观测古代个体的遗传成分和基因的混杂模式,让化石讲述他们所历经的故事。通过比较古生物和现代生物之间遗传的差异和联系,比如遗传差异或生物谱系关系,揭示人类演化过程、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细节。通过分析古细菌、古病毒基因组,了解致病菌遗传变异规律等信息,从而更好制定防治策略。
斯文特・帕玻是古DNA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最初对古DNA感兴趣是为了研究古埃及木乃伊的DNA。还在进行人体免疫蛋白相关博士课程研究的他,跑去位于当时东德的一家博物馆收集木乃伊样品。通过一系列实验,自认为提取到古代DNA后,他的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包括让大部分科研人士羡慕的《自然》杂志等学术刊物上。
不过,后来的研究发现,古DNA其实很容易被现代人的DNA所污染。由于当时帕玻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设计方案控制污染,所以他最初几篇论文所发现的“木乃伊DNA”至少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DNA污染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三星堆这次参与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为何穿防护服。
污染的控制和识别是古代DNA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古DNA分子的提取非常困难。DNA储存在细胞核内,生物体在死亡过程中,细胞就会逐渐发生自溶,DNA很快会被降解。在高温和潮湿的条件下,DNA自身也容易发生水解、断裂。同时,即便有细胞保存下来也会碰到其它微生物的进驻,所产生的酶类也会把原细胞内的DNA破坏掉。由于古生物没有特别的存储条件,在自然环境下,DNA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不容易。
这些原因使得古DNA基因序列片段比现代DNA更短,所以,古DNA测序比现代DNA也要更复杂。不仅读取、比对的数据量更大,对计算力的要求也更高。数据清洗、测序过程中,还需要用到非常多的不同于现代DNA测序的应用软件,如何实现这些应用软件的快速移植与开发也是一大挑战。
百年沧海桑田,早已换了人间。
近年来,被誉为“下一代测序技术“的“高通量测序技术”一次能并行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DNA分子进行快速测序分析,以低成本、99% 以上的准确度,使得对一个物种的转录组和基因组进行细致全貌的分析成为可能。